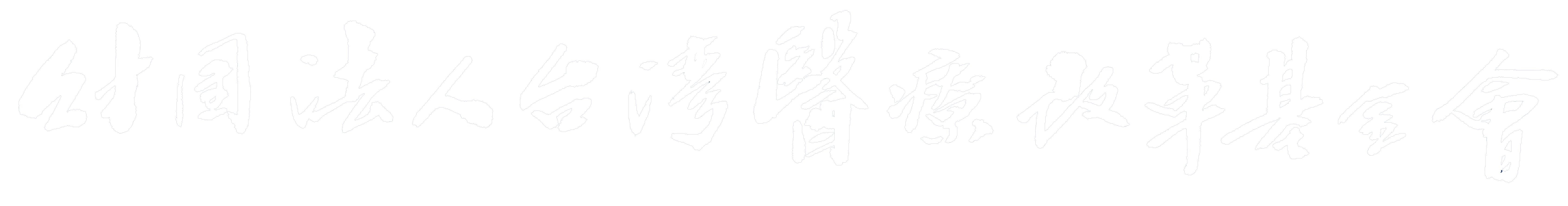病歷中文化不只是醫師的責任
黃嵩立(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秘書長、陽明大學公衛所教授)
病歷中文化的爭議點之一,在於病歷書寫之目的。將病例內容簡單分類,第一類包括各種同意書、住院摘要、診斷證明等,理當使病人理解,目前已規定以中文為之。第二類是各種檢查報告。簡單的例如血紅素、潛血反應等;病人可從數據去查閱自己是否處於正常範圍,僅需將檢驗項目中文註記即可。較為複雜的,例如影像學檢查、病理檢查等諸多報告,專業術語最多,病患自行閱讀的障礙其實來自專業知識的高門檻。這類報告的中文化,難度最高。
第三類,是醫師對門診或住院病人的病情和處理之簡要紀錄,包括對病情的評估、病人對治療的反應等等,記載目的主要是為了日後臨床工作之參考,是以專業同儕為目標。醫師慣常使用簡寫、縮寫、甚至醫學領域專用的語法,令人難以索解。此部分恐怕是病歷中文化爭議最多之處:中文化的預設目標是要使病歷成為可供病人研讀的材料。但如果病歷目的不同,病歷記載的方式就必須大幅改變。為了讓一般人看懂,醫師必得仔細書寫,縱非字斟句酌,至少要做到清晰明瞭,以預防病人質疑和法律爭議。長期來看,鼓勵醫師做好記錄,絕非不值得追求的目標。
一個可能的論點是,在專業隔閡不能降低的情況下,語文隔閡具有避免誤解的保護作用。部分醫師憂心,病人或家屬可能無法理解診斷和治療是一個不斷更新、變動的過程。如果病歷是中文,病人將會如何開始閱讀「看得懂、但可能造成誤解」的一本記錄?有沒有可能被過度解讀?病人又將如何將散在病歷各處的各種報告拼湊出全貌?將一堆資料都放進谷歌搜索,將會產生多少可能的鑑別診斷?後見之明,是否將挑戰先前的臨床判斷?病人一旦習於檢視中文病歷,造成醫病誤解的機會是否大增?這些顧慮或許為真,然而其癥結是在醫病相互信任;讓語言隔閡多增醫病溝通之障礙,恐怕無助於問題之消解。
現階段病歷中文化有些許困難,其中,醫學專用名詞的統一,是政府該設法解決的問題。在病歷輸入時同時帶出中、英文雙語,是醫學資訊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。但目前最難解決的是,醫師耗費了大量時間於文書工作,如果因為是中文,而讓病人覺得應該要人人看得懂,那麼醫師的文書工作量將何止倍增。同時,以挑錯為出發點的病歷審閱,也增加醫師的執業成本。然而,語文障礙不應成為專業隔閡的防禦工事。病歷中文化的討論,點出醫師工作量、病歷記載方式、病歷品質、醫病溝通等問題。
台灣長期依賴醫師們的超級效率,以偏低的醫療成本享受物超所值的服務。但是此種效率有其代價,其中之一就是簡要而不盡完整的病歷記載方式。醫界整體、健保局、所有繳納健保費的國人,都必須更尊重醫師花費在病歷記錄和醫病溝通的時間成本。醫師、護理師經常利用「下班」時間補寫病歷,幾乎被視為常態;中文化的要求將迫使第一線醫師面對來自院方和病人的雙重壓力。病歷中文化本身已經是相當複雜的議題,但它無法與醫療品質的其他面向脫鉤討論。中文化是有助於保障病人權益的步驟,但是這不單是醫師們的責任。立法者和醫院經營者,在此時應該要有大幅審視病歷品質、改善工作條件的準備,才可能締造醫病雙贏的條件。
(本文刊載於 104.01.20 蘋果即時論壇,內容經作者小幅修正,
並經作者同意授權本會轉載,特申謝忱。)
並經作者同意授權本會轉載,特申謝忱。)